六月十六日清晨,县作协一行三十余人驱车来到大畈镇大墈村,然后步行翻越鸡口山,重走当年红军用鲜血染红的山路。

以大墈村作为此次徒步的起点,意义非凡。因为早在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通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在此地召开。它见证了共产党在通山的发展壮大。
八点五十分,我们从大墈村出发,向里处的鸡口山方向行进。经过一段五米宽的水泥公路,鸡口山麓已映入眼帘,抬头仰望,看不到山顶。大家既兴奋又激动,整了整行装,准备登山。据说要走二个小时的山路,有的同伴赶忙在路边寻找可以充当临时拄杖的棍子。作为队伍里的年轻人,我跃跃欲试,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在队伍的前面,迫不及待地去感受这条从未走过的红军路。

一开始是上山。由于鸡口山挡住了阳光,我们得以穿梭在阴凉的树荫里,沿着二、三尺宽的弯曲山路一直向上走,时而跃过一条山沟,时而抓藤攀爬。林中传出阵阵雀声,急促而悠扬,像冲锋号一样,提醒大家不要掉队。半个多小时后,不少同伴气喘吁吁,示意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边埋怨自己平常锻炼不够以致体能下降,边感慨当年老一辈跳着箩担干革命的艰辛。我们走在前面的几个“先遣队员”停了下来,与身后的大队会合,坐在山涧边的石阶上,开始聆听党史办王振华同志讲党史。其口述内容大都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国民党围剿红军时期,大畈镇和黄沙铺镇的革命人士依托鸡口山这条要道互通联系,在外部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顽强生存。正是脚下的这条山路传递了从莫斯科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递了共产主义信仰……
有的同伴边听边喝起涧泉水,凛冽又爽口。我们突然意识到这条山间流淌下的清泉不仅滋养了穿梭于两镇间的祖祖辈辈,滋养了当年的革命者,也滋养了这条路上的每一个生灵。

听完口述,大家有点不好意思,遂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赶路,计划在气温未升高前到达山顶。
我们几个“先遣队员”依旧走在最前面,为大队开路。很快就到达鸡口山石门。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产物,像是有三块巨石拼成的门状洞口,外观像是一只鸡。也许鸡口山名的由来跟这个石门有点渊源吧。会师后,大伙在石门前稍作逗留,拍照留念。我也到石门外摆拍起来。这时,一个健壮的汉子赶着一群黄牛向人群走来。前面的三只公牛显然警惕起来,不进不退,用充满敌意的眼神望着我们。三只公牛后面还跟了两只小黄牛,也跟着停了下来,甚至向后退。当时的我站在窄路边,靠那仨很近,头上又恰好带了顶红色的帽子,所以紧张了起来,毕竟如此近距离的面对三只惊恐中的公牛。那汉子笑了笑,向我示意不用担心。僵持了数分钟后,牛群见大伙没有恶意,便在汉子的叫喊声中迈开了步子,一下子就消失在视线里,只听得牛铃声越来越小。
当时的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我们也自认为是唯一的一支队伍。深山密林中突然出现的汉子和他的牛群,让人不禁感叹: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离开石门,我们很快登山山顶,大畈镇和黄沙铺镇的交界处就在脚下。穿过茂密的黄金楝,沿途看见供电工人布下的电缆线,听见若远若近的牛铃声,向前方的远山望去,革命老区黄沙铺镇已在目中。
继续向下走,大家在一个破旧的凉亭附近再次歇脚。“看,泡桐树!那是我老家一个扶贫户前年种的,现在已经成参天大树了。”一个坐在凳状石头上的同伴叫道。
“是啊,泡桐树长得很快的。你可以叫他联系林场探探销路。我接过话茬子,又说:“如今扶贫政策好,你跟他说说。”
离开凉亭,就到鸡口山脚下了,已经能看见远处的穿山高速公路,下面有一根根泡桐般的钢筋混泥土柱子将高速公路稳稳撑起。整体看上去,像巨人搴起裤管在插秧。而“脚下”正是黄沙铺镇的万座楼房,犹如巨人插入田中的万茎秧苗。

出了鸡口山,沿着杭瑞高速公路出口,大伙在疲惫中带着感动,望着身后的鸡口山,渐行渐远。感慨它不仅见证了数千年的雨雪风霜,还见证了当年红色信仰在大畈、黄沙铺间的传递,见证了当年数千热血青年抛家舍业干革命的光荣,见证了革命老区的沧桑巨变。
个人简介

杨鑫,男,湖北通山人,通山县作家协会会员,通山县李自成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供职于县编办。热爱学习,低调做人,本分做事。最大的爱好是阅读,尤爱研史。座右铭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争做一个有益于通山文史发展和廉政建设的热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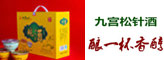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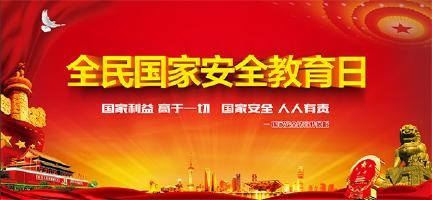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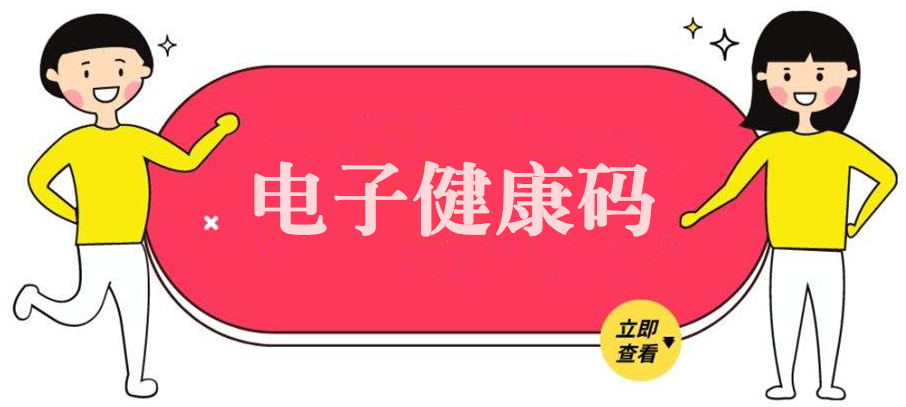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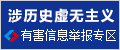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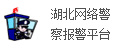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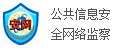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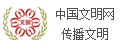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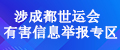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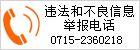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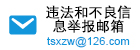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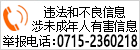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0~2017
Copyright © 2010~2017 
